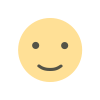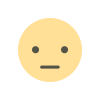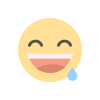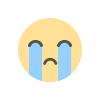【專欄】中華思想是引爆東亞戰爭的導火線
在西方勢力來到東方之前,華夷思想與朝貢体制是東亞國際秩序的基本結構。中國共產黨本來是要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框架,而建立起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是自習近平上任之後,他強調要復興偉大的中華民族,而這使得東亞的國際秩序一直處在大國的威嚇之中,台灣每次選舉永遠脫離不了中國介選的夢靨。但是當中國處在強人統治之下時,中國人民永遠要處在因為政策錯誤所造成的貧困當中。或許改變東亞大國的思想是改變東亞國際秩序所必須要思考的課題,這應該是新思想的出發點。 其實在華夷思想的結構之下,並不是所有的夷狄都甘為化外之民,日本就是其中一例。而這正是現代各個國家平等的國際秩序的先驅。 一.日本與「中華」的對峙—從自我認識的觀點來看 「中華」這個用語源自古代中國,這是漢族建立周王朝時的自己稱呼與自我認識。與這個用語同時成立的是包圍中華的「夷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用語。這個用語是將周圍的國家認為是與自己不同,是劣等(野蠻)的,因此這個用語是一種對他者的認識。如果把兩者綜合起來的話,這個用語所代表的思想就稱之為「華夷(思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自民族(或是自我集團)中心主義。 當我們進一步思考「中華」的意義時,一個意義是地理上的概念,亦即是中華是「世界的中心・中央」,另一個意義是文化上的概念,亦即是儒教文化的極致。日本教授小池喜明將前者稱為「固定的華夷思想」,這是透過地理的因素而使華夷之別絕對化與固定化的思想;而後者則是不使用地理的因素,僅以文化的標準來區分華夷,這被稱理為「流動性的華夷思想」,是屬於方法論的「華夷思想」。後者的思維方式特別在理解日本人的自我認識與對外思想上面是有效的。 華夷思想的理論是:儒教文化的精隨位處於天下的中心・中央(周王朝/漢族),隨著離開這個中心,儒教文化(最終來說就是天子的德)就越離越遠而無法到達,因此這些地方就變得是相對劣等之處(其離最遠的邊緣是「徳化之外」・禽獣)。此外,「夷狄」向「中華」朝貢,而「中華」則冊封「夷狄」,這就形成了一種以儒教為基礎的(道德上的)統治。在歷史上,由於「中華」一直是由中國的王朝獨佔並君臨,因此圍繞著這一個「中華」的「夷狄」就只能不斷地與這兩種「中華」對峙,而以此去形塑他們自己本身。 換句話說,在固定的華夷思想當中,「中國」一直是「中華」,而周邊國家一直是「夷狄」。只要中心是「中國」時,朝鮮和日本就被迫要接受自己是「東方的國家・夷狄」的這個自我認知。如果要擺脫這種認知,就必須自己成為中心。但是,在流動的華夷思想當中,則情況並非如此。因為隨著「中華」的基準發生變化,「夷狄」也有可能成為「中華」。 在十七世紀初期,漢族的明朝(中華)被滿洲族的後金・清朝(夷狄)所滅亡,這種「夷狄」變成「中華」的現象就被稱為「華夷變態」。由於「中華」的地位和中國的領土被『到目前為止被認為是「夷狄」之人』在物理上加以占據,所以從先前的分類來看,這會是固定的華夷思想的一種發展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周邊國家對此並不會完全接受。 例如朝鮮的情況即是。從高麗末期開始,朝鮮就致力於儒教(朱子學)的接受,在明朝時期,朝鮮更加努力實踐並正確進行對於儒教的理解,並自己認為自己是次於明朝的國家。縱然朝鮮受到軍事威脅而被迫向清朝行三跪九叩頭的禮節致敬,並不得不朝貢,但明朝滅亡後,朝鮮就產生了小中華意識,認為中國的精髓、儒教文化的繼承者唯有朝鮮,而不是滿洲族的清朝。這甚至使得在通俗上被理解為是「尊文輕武」的朝鮮在十七世紀後半出現北伐論,主張為了對明朝報恩而要討伐清朝位明朝復仇。 在朝鮮成為「小中華」的過程,基本上是在本家「中華」空缺的前提之下而進行的,而「中華」的基準從向來的儒家的觀點來看,並未有改變。就朝鮮的情況來看,他們對峙的是「夷狄的中華」,而不是「中華」本身。 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情況下,根據桂島宣弘的說法,十七世紀前半期之前,以儒教為基準的「禮・文中華主義」(即中華是指中國)在明清交替後的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前半,逐漸出現了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型華夷思想」,這個思想雖然保留了傳統的基準(中華),但強調了「日本」的優越性,並在十八世紀後半的垂加神道思想當中,成為顯著的「日本中華主義」。然而,這些變化仍然是受到儒教的影響,這個「日本中華主義」直到十九世紀國學思想的興起,才實現了對「中華・中國」的脫離。 與朝鮮不同,日本在與「中華」對峙時,進行了克服的努力。由於日本未向清朝朝貢,所以對「中華」並沒有顧慮,但只要「中華」概念的軸心仍然是在儒教的話,日本就無法占有「中華」的位置。因此,日本就自己成為「中華(中心)」,而脫離儒教,提出了「武威」和「萬世一系的天皇」等不同的標準。在鴉片戰爭清國戰敗之後後,佐藤信淵表示「滿清也是夷狄,英吉利亞也是夷狄」,並表明了希望清國永遠為本邦之西屏,這顯示出日本對「中華・中國」的脫離。 日本所對峙的「中華」並非僅僅是自我認識。在近代,要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日本再次碰到了「中華」這個障礙。這個障礙不僅僅是清朝,還包括了清朝所建立的朝貢體制本身。其中一個具體的衝突場景就是:在近代過渡時期的對朝鮮外交當中(另外一個場合是琉球),所發生的兩個主要的衝突,一是「西方式的國家關係.外交秩序」與「中華秩序(即透過朝貢關係所建立的宗主國—屬國關係)」的衝突,另一個是與朝鮮進行外交談判的衝突。最後日本以戰爭解決了中華思想無法與近代西洋思想倂容的問題,而當然這也留下了後遺症。 二、中國必須解構中華思想 中華思想從周邊國家來看,是損害它們的許多利益,也帶來了許多的屈辱。但是中國只要在中華思想之下,就始終會追求大一統而成為世界的夢靨。因此,中國必須走上能夠並立的地方分權國家體制,這才有可能在東亞與東南亞建立真正平等的國際秩序,否則只要中國不亂,台灣就必須受中國的恐嚇與威擾,這是台灣人必須思考的課題。


在西方勢力來到東方之前,華夷思想與朝貢体制是東亞國際秩序的基本結構。中國共產黨本來是要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框架,而建立起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是自習近平上任之後,他強調要復興偉大的中華民族,而這使得東亞的國際秩序一直處在大國的威嚇之中,台灣每次選舉永遠脫離不了中國介選的夢靨。但是當中國處在強人統治之下時,中國人民永遠要處在因為政策錯誤所造成的貧困當中。或許改變東亞大國的思想是改變東亞國際秩序所必須要思考的課題,這應該是新思想的出發點。
其實在華夷思想的結構之下,並不是所有的夷狄都甘為化外之民,日本就是其中一例。而這正是現代各個國家平等的國際秩序的先驅。
一.日本與「中華」的對峙—從自我認識的觀點來看
「中華」這個用語源自古代中國,這是漢族建立周王朝時的自己稱呼與自我認識。與這個用語同時成立的是包圍中華的「夷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用語。這個用語是將周圍的國家認為是與自己不同,是劣等(野蠻)的,因此這個用語是一種對他者的認識。如果把兩者綜合起來的話,這個用語所代表的思想就稱之為「華夷(思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自民族(或是自我集團)中心主義。
當我們進一步思考「中華」的意義時,一個意義是地理上的概念,亦即是中華是「世界的中心・中央」,另一個意義是文化上的概念,亦即是儒教文化的極致。日本教授小池喜明將前者稱為「固定的華夷思想」,這是透過地理的因素而使華夷之別絕對化與固定化的思想;而後者則是不使用地理的因素,僅以文化的標準來區分華夷,這被稱理為「流動性的華夷思想」,是屬於方法論的「華夷思想」。後者的思維方式特別在理解日本人的自我認識與對外思想上面是有效的。
華夷思想的理論是:儒教文化的精隨位處於天下的中心・中央(周王朝/漢族),隨著離開這個中心,儒教文化(最終來說就是天子的德)就越離越遠而無法到達,因此這些地方就變得是相對劣等之處(其離最遠的邊緣是「徳化之外」・禽獣)。此外,「夷狄」向「中華」朝貢,而「中華」則冊封「夷狄」,這就形成了一種以儒教為基礎的(道德上的)統治。在歷史上,由於「中華」一直是由中國的王朝獨佔並君臨,因此圍繞著這一個「中華」的「夷狄」就只能不斷地與這兩種「中華」對峙,而以此去形塑他們自己本身。
換句話說,在固定的華夷思想當中,「中國」一直是「中華」,而周邊國家一直是「夷狄」。只要中心是「中國」時,朝鮮和日本就被迫要接受自己是「東方的國家・夷狄」的這個自我認知。如果要擺脫這種認知,就必須自己成為中心。但是,在流動的華夷思想當中,則情況並非如此。因為隨著「中華」的基準發生變化,「夷狄」也有可能成為「中華」。
在十七世紀初期,漢族的明朝(中華)被滿洲族的後金・清朝(夷狄)所滅亡,這種「夷狄」變成「中華」的現象就被稱為「華夷變態」。由於「中華」的地位和中國的領土被『到目前為止被認為是「夷狄」之人』在物理上加以占據,所以從先前的分類來看,這會是固定的華夷思想的一種發展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周邊國家對此並不會完全接受。
例如朝鮮的情況即是。從高麗末期開始,朝鮮就致力於儒教(朱子學)的接受,在明朝時期,朝鮮更加努力實踐並正確進行對於儒教的理解,並自己認為自己是次於明朝的國家。縱然朝鮮受到軍事威脅而被迫向清朝行三跪九叩頭的禮節致敬,並不得不朝貢,但明朝滅亡後,朝鮮就產生了小中華意識,認為中國的精髓、儒教文化的繼承者唯有朝鮮,而不是滿洲族的清朝。這甚至使得在通俗上被理解為是「尊文輕武」的朝鮮在十七世紀後半出現北伐論,主張為了對明朝報恩而要討伐清朝位明朝復仇。
在朝鮮成為「小中華」的過程,基本上是在本家「中華」空缺的前提之下而進行的,而「中華」的基準從向來的儒家的觀點來看,並未有改變。就朝鮮的情況來看,他們對峙的是「夷狄的中華」,而不是「中華」本身。
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情況下,根據桂島宣弘的說法,十七世紀前半期之前,以儒教為基準的「禮・文中華主義」(即中華是指中國)在明清交替後的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前半,逐漸出現了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型華夷思想」,這個思想雖然保留了傳統的基準(中華),但強調了「日本」的優越性,並在十八世紀後半的垂加神道思想當中,成為顯著的「日本中華主義」。然而,這些變化仍然是受到儒教的影響,這個「日本中華主義」直到十九世紀國學思想的興起,才實現了對「中華・中國」的脫離。
與朝鮮不同,日本在與「中華」對峙時,進行了克服的努力。由於日本未向清朝朝貢,所以對「中華」並沒有顧慮,但只要「中華」概念的軸心仍然是在儒教的話,日本就無法占有「中華」的位置。因此,日本就自己成為「中華(中心)」,而脫離儒教,提出了「武威」和「萬世一系的天皇」等不同的標準。在鴉片戰爭清國戰敗之後後,佐藤信淵表示「滿清也是夷狄,英吉利亞也是夷狄」,並表明了希望清國永遠為本邦之西屏,這顯示出日本對「中華・中國」的脫離。
日本所對峙的「中華」並非僅僅是自我認識。在近代,要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日本再次碰到了「中華」這個障礙。這個障礙不僅僅是清朝,還包括了清朝所建立的朝貢體制本身。其中一個具體的衝突場景就是:在近代過渡時期的對朝鮮外交當中(另外一個場合是琉球),所發生的兩個主要的衝突,一是「西方式的國家關係.外交秩序」與「中華秩序(即透過朝貢關係所建立的宗主國—屬國關係)」的衝突,另一個是與朝鮮進行外交談判的衝突。最後日本以戰爭解決了中華思想無法與近代西洋思想倂容的問題,而當然這也留下了後遺症。
二、中國必須解構中華思想
中華思想從周邊國家來看,是損害它們的許多利益,也帶來了許多的屈辱。但是中國只要在中華思想之下,就始終會追求大一統而成為世界的夢靨。因此,中國必須走上能夠並立的地方分權國家體制,這才有可能在東亞與東南亞建立真正平等的國際秩序,否則只要中國不亂,台灣就必須受中國的恐嚇與威擾,這是台灣人必須思考的課題。